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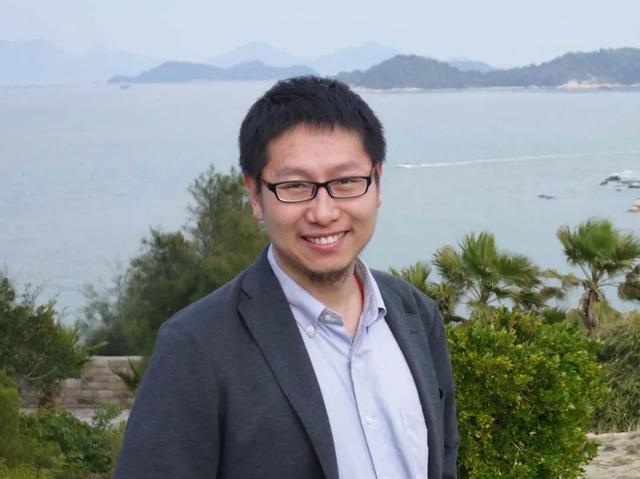
摘要:理学家认为“和气”是对现实政治状态的反应,朱子直接讨论感召和气,往往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认为荒政需要感召和气,解决政治问题的根本需要君主正心诚意以立纲纪,最终感召来和气。心术是立纲纪和召和气的关键,君主承担天下,君主之心能影响天下之气,但士大夫则可以通过“格君心之非”来起到感召和气的作用。当然,朱子讲的感召和气并不同于汉儒天人感应的模式,他更强调人的心性修养与自然和气之间的关联。理学工夫是能够感召到和气的入手处。
关键词:和气 纲纪 心术 致中和 天地之气
邓小南先生在论述宋代“祖宗之法”时,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指出,“宋代‘祖宗之法’的主要目标,在于保证政治格局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它以感召‘和气’为念,希望庶政平和而警惕变乱的代价。基于这一立意,宋代士大夫始终关心‘纪纲’建设,充分贯彻着维系制约的原则”,“所谓‘立纪纲’,在宋人心目中指的是订立制度;‘召和气’,则是指能够感召天地,使万事万物充盈着雍睦和谐的自然之气。两端并行并举,相辅相成”。[1]在以往的朱子政治哲学或政治思想研究中,“立纲纪”是关注的重点,这在对以“封事”为代表的朱子争论性文本的诠释中,表现得尤为突出,[2]而对“召和气”关注则较少。关注“立纲纪”较多,似与朱子直接地、系统地谈“纲纪”的地方较多有关,朱子明确讲过,“夫所谓纲者,犹网之有纲也;所谓纪者犹丝之有纪也。网无纲则不能以自张,丝无纪则不能以自理”[3],只有确立了纲纪,才能抓住国家治理的关键。相对应地,朱子对“和气”的直接论述却不多,似未明确对什么是和气给予特别的说明。但是,如果把对问题的关注不限于“和气”这样直接的表达,而关注朱子对天地、万物和谐的自然之气的阐发,就会发现朱子对“和气”的关注度并不弱。特别是结合朱子的经典诠释,就会发现朱子对《中庸》“致中和”等的诠释,均与“感召和气”这一问题有关。
“感召和气”涉及政治主体的“心”对现实政治秩序的影响,对天地万物状态的影响,涉及朱子面临现实具体政治问题时的态度与对策。对朱子思想中“感召和气”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其思想中“心与气”的政治哲学向度。
一、政与气
在宋代理学的语境中,“和气”是对现实政治状态的反应,天地万物之气是否“和”则影响现实中人、事、物的“禀气”以及后天成长,如周敦颐《通书·乐中第十八》讲:
乐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则天下之心和。故圣人作乐,以宣畅其和心,达于天地,天地之气,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则万物顺,故神祇格,鸟兽驯。[4]
朱子注言:
圣人之乐,既非无因而强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声气之元。故其志气天人交相感动,而其效至此。[5]
在周敦颐看来,圣人之乐与现实的政治治理状态关系密切,如果治理得法、百姓心安,那么天下的人心就“和”,这样的人心通过“乐”表达出来就会影响天地之气,达到至高的和谐状态,如此就会使得宇宙的各种存在都达到和谐状态。朱子的注释特别强调“志气天人交相感动”,即认为现实的政治能够影响人心、影响天地之气,而天地之气反过来又会影响现实的人。
二程也讲:
古人虽胎教与保傅之教,犹胜今日庠序乡党之教。古人自幼学,耳目游处,所见皆善,至长而不见异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见皆不善,才能言便习秽恶,日日消铄,更有甚天理!须人理皆尽,然尚以些秉彝消铄尽不得,故且恁过,一日之中,起多少巧伪,萌多少机阱。据此个薰蒸,以气动气,宜乎圣贤之不生,和气之不兆也。寻常间或有些时和岁丰,亦出于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时或同家并生圣人,及至后世,乃数千岁寂寥?[6]
古人由于有学、有教,因此容易成就,按照这里的逻辑,由于人人由教而善,和气亦能“兆”。而后世由于圣人之教的缺失,人人禀得的天理在现实中无法展现,机巧之心日生,而导致现实的“气”不和谐。在这样的“气氛”影响下,圣贤就不容易诞生,年景也不能保持长久的丰饶,偶尔遇到丰年,也是侥幸。[7]在这里,人是否成善能够影响天地之气的状态,而反过来,天地之气的状态又对现实的人产生作用。《河南程氏外书》亦有:
《酉室所闻》云:“颜子得淳和之气,何故夭?”曰:“衰周天地和气有限,养得仲尼已是多也。”圣贤以和气生,须和气养。常人之生,亦借外养也。[8]
2023年6月递交上市申请材料至今,山大电力尚未完成问询。8月9日,深交所向山大电力发出第三轮审核问询函。

标题:商标权权属纠纷民事一审裁定书
审理法院:江苏省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案由:商标权权属纠纷
裁判结果:本案按原告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撤回起诉处理。
当事人信息:
原告: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被告:陈某
判决日期:2024年1月30日
数据来源:企查查(当事人公司/机构全名是通过与相关诉讼立案主体关联获取的)
圣贤禀得天地之和气以生,但初禀天地之气以“生”之后还需要天地之气整体的滋养,如果天地之气不和,那就会使得圣贤“大德不受命”。天地之气不仅影响圣人的后天状态,对平常人亦有影响。人、人心与天地之气的交互影响,是以周敦颐、二程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的基本观点。
朱子在直接讨论“感召和气”时,往往与现实政治问题相关,特别是与“荒政”有关。与“和气”相对的是“乖气”,现实的表现就是“灾异”。现实政治治理得好,则会感召和气,反之则会感召乖气,乖气盛则灾异不断。面对灾异,需要“君臣相戒,痛自省改,以承皇天仁爱之心,庶几精神感通,转祸为福”(20,787),“转祸为福”即是变乖气为和气,前提是政治主体的“心上功夫”。
李华瑞教授指出,“感召和气,以致丰穰,是朱熹荒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9]。朱子的政治实践多与荒政有关,在《论灾异札子》《乞修德政以弭天灾变状》等奏札中均有对“感召和气”的强调。《朱子语类》言:
“而今救荒甚可笑。自古救荒只有两说:第一是感召和气,以致丰穰;其次只有储蓄之计。若待他饥时理会,更有何策?东边遣使去赈济,西边遣使去赈济,只讨得逐州几个紫绫册子来,某处已如何措置,某处已如何经画,元无实惠及民。”或问:“先生向来救荒如何。”曰:“亦只是讨得紫绫册子,更有何策!”[10]
面对“救荒”,只采取赈济手段,都是临时性措施,而不是直指“荒政”的根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要“感召和气”,也就是通过对政治的改善、人心的改变,使得天地之气和,如此则丰穰之年常见,而不会有连续的荒年出现;二则要做好“储蓄”,也就是做好应对荒年的物质准备。从朱子的论述来看,“感召和气”其实是“储蓄”的根本,没有年景的丰穰,“储蓄”也就不可能,而具体的救灾举措,更是迫不得已的举措。正如李华瑞教授所讲,“当天子、臣属、百姓其心皆圣,阴阳相和,自然就不会有灾异发生,但在人世间,私欲不尽,天理还不畅明时,精祈祷、敬鬼神往往难以感通上苍,毕竟灾荒频仍。这时,唯一的补救措施,‘莫若宽其税赋,弛其逋负,然后可以慰悦其心而感召和气也’”[11]。《朱子语类》此说,是朱子政治实践的总结,他“在地方为官时为正人心、厚风俗,诚心敬意祈祷当地山川雷雨之神,为百姓召和气、禳弭灾”[12]。面对自然灾害,朱子本人并不完全反对“祈雨”等传统手段,但重要的不是“形式”,而要从“心”入手,“祈雨之类,亦是以诚感其气”[13],没有“诚敬之心”,就不可能对现实的气运产生改变——没有诚敬之心,而仅有巫觋、祭祀、礼乐等形式,在理学家看来,气是无法改变的。
上文已经指出,朱子实践的“召和气”、面对荒年采取的手段,按其逻辑,还不是从根本入手,而只是一时一地的为政手段。《朱子语类》言:
问:“三代规模未能遽复,且讲究一个粗法管领天下,如社仓举子之类。”先生曰:“譬如补锅,谓之小补可也。若要做,须是一切重铸。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县,其法无一不弊,学校科举尤甚。”又云:“今之礼,尚有见于威仪辞逊之际;若乐,则全是失了!”问:“朝廷合颁降礼乐之制,令人讲习。”曰:“以前日浙东之事观之,州县直是视民如禽兽,丰年犹多饥死者!虽百后夔,亦呼召他和气不来!”[14]
如果根本的政治治理格局不能确立,现实的治理手段只是小修小补。“重铸”即回到根本,全盘解决政治问题。朱子对现实政治颇为不满,认为南宋的政治治理,不要说荒年,哪怕是丰年,百姓也会有饿死的。如果根本的政治局面不改变,即使有上百个夔这样的人物,也没有办法召来和气——能不能召来和气,不能只靠少数贤人,朱子在当时仅相当于一夔耳,他能改变他为政地区一时的问题,但还不是根本。要能根本地感召和气,变乖气为和气,则要直面政治的根本问题,直面君心,需要君主正心诚意以立纲纪,恢复三代规模,才能全盘解决政治问题,改变天下人心。
二、心术、纲纪与和气
“召和气”需要“立纲纪”,“立纲纪”则需要君主正心诚意,[15]人臣除了自身修养之外,能够“格君心之非”。无论是立纲纪还是召和气,都要在乎心术的作用。朱子在《太极说》中讲“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达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23,3274),这里以为心是致中和的关键。感召和气,是通过人心的变化,使得感应可以发生。在朱子的感应论中,“‘心’既是感应发生的场所,也是工夫修养以促成和实现感应的起点,因而关于‘心’的修养和护持是感应顺畅的关键”[16],而使得感应发生的关键条件则是“诚”,“感应的实现绕不开‘诚’。‘诚’在工夫论上是一种真实无伪的心理状态,是感应发生的心理和情感基础”[17]。如是,心是“和气”能否被感召最重要的工夫场域。
特别是从政治实践主体出发,人主之心术是能否感召和气的关键。朱子在《孟子集注》中解释“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时,引程子之语表达自己的观点:“程子曰:‘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君之仁与不仁耳。心之非,即害于政,不待乎发之于外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谏之。然非心存焉,则事事而更之,后复有其事,将不胜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后复用其人,将不胜其去矣。是以辅相之职,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后无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则亦莫之能也。’”[18]即认为君主之心仁与不仁是国家治乱的关键,是一切具体事务的核心抓手,君主能够知是非,就能使天下的政治有所保障。《壬午应诏封事》讲:“人君之学与不学、所学之正与不正,在乎方寸之间,而天下国家之治与不治,见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系岂浅浅哉!”(20,572)此“方寸之间”即心。《庚子应诏封事》则以为“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20,586)。《戊申封事》则以为“陛下之心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20,590)。君主之心是国家治与不治的关键,按照上文逻辑,也是感召和气的关键。反之,如果君主之心术不正,国家之纲纪不立,则可能招致灾异。
《庚子应诏封事》以为,如果君主不恤民、不爱民,就会使国家“元气日耗,根本日伤,一旦不幸而有方数千里之水旱,则其横溃四出,将有不可如何者”(20,582),灾害产生即是乖气横行。在《辛丑延和奏札》中,朱子列举了君主应当反省的十个问题,诸如“德之崇者有未至于天欤”(20,638),这些均与朱子理解的纲纪有关,而直指君主之心,然后讲“夫必有是数者,然后足以召灾而致异”(20,638),即做到了朱子所讲的那些,就能召来和气,反之则会有灾异。在该奏札中朱子强调“日往月来,浸淫耗蚀,使陛下之德业日隳,纲纪日坏,邪佞充塞,货赂公行,兵怨民愁,盗贼间作,灾异数见,饥馑荐臻”(20,641)。如果君主反省得当,并从心出发“立纲纪”,则“使一日之间云消雾散,尧天舜日廓然清明,则上帝鬼神收还威怒,群黎百姓无不蒙休矣”(20,638),此即和气被感召到的一种描述。
君主之心乃至君主的行为,何以有如此重要的影响?这与君主对天下的担当有关,“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极之标准于天下也”(24,3454—3455),君主的行为会成为天下的表率,朱子将“皇级”解释为“盖皇者,君之称也;极者,至极之义,标准之名”(24,3454),即与对君主的职责、地位的强调有关。[19]更为明确的,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君主之心与天下之气联系在一起,《朱子语类》有:
叔器问:“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此是分当如此否?”曰:“也是气与他相关。如天子则是天地之主,便祭得那天地。若似其他人,与他人不相关后,祭个甚么?如诸候祭山川,也只祭得境内底。”[20]
“所当祭者,其精神魂魄无不感通”(22,2467),君主当祭天下,既有合礼性,又是天地之理的规定。天下之气与君主相关,君主是天地之主,因此能够影响得了天下的气运,而君主之心又是君主之身的主,如此,回归根本,就更要在乎君主之心:
或问:“致中和,位天地,育万物,与喜怒哀乐不相干,恐非实理流行处。”曰:“公何故如此看文字!世间何事不系在喜怒哀乐上?如人君喜一人而赏之,而千万人劝;怒一人而罚之,而千万人惧;以至哀矜鳏寡,乐育英才,这是万物育不是?以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长幼相处相接,无不是这个。即这喜怒中节处,便是实理流行,更去那处寻实理流行!”[21]
君主的喜怒哀乐不仅仅是自身的情绪表达,朱子将之上升到“实理流行”,也就是天理彰显的高度。朱子认为,君主的情绪会实实在在地影响到天下的人、事、物。[22]
当然,如果要让天地之气发生变化,就不仅仅需要君主担当,而需要人人都能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作用。《朱子语类》一段谈及当时之事,兼及经典、史事,颇能代表朱子的相关看法:
因言:“淮上屯田,前此朝廷尝差官理会。其人到彼,都不曾敢起人所与者。都只令人筑起沿江闲地以为屯,此亦太不立。大抵世事须是出来担当,不可如此放倒。人是天地中最灵之物,天能覆而不能载,地能载而不能覆,恁地大事,圣人犹能裁成辅相之,况于其他。”因举齐景公答夫子“君君臣臣”之语,又与晏子言“美哉室”之语,皆放倒说话。且如五代时,兵骄甚矣。周世宗高平一战既败却,忽然诛不用命者七十余人,三军大振,遂复合战而克之。凡事都要人有志。[23]
这里论及南宋在安徽淮南的屯田,朱子以为主事者不担当,导致事不成。在朱子看来,人是天地之灵,有“灵”就要有承担。圣人可以对天地之事进行“裁成辅相”,成就天地之事,对于具体的事,主事者若担当,都能有所成就。春秋时的齐景公即是“放倒”,不担当。五代时,周世宗面对危局,担当起来,反而能成事。当然,周世宗还不是朱子眼中能够做到正心诚意的君主,还不能使天地之气真正达到太和,即便如此,世宗的担当,也足够使局面发生变化。
三、致中和
以上着重从政治治理的角度讨论了朱子如何看待“感召和气”。其实如果从经典解释出发,就会看到朱子思想中的“感召和气”与他对《中庸》“致中和”等经典的诠释密切相关。理解朱子对“致中和”的解释,可以深化上文对政与气、心术与和气关系的思考。
《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章句》注言:
致,推而极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故其效验至于如此。此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初非有待于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体一用虽有动静之殊,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则其实亦非有两事也。故于此合而言之,以结上文之意。[24]
在《中庸》的语境中,“和”原本指“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的状态,但这里讲了“致中和”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因此对这句话的诠释也就涉及天地万物之和,涉及天地的“和气”。在朱子看来,个体的戒慎恐惧工夫如果达到极致,就可以使天地安其所、万物遂其生。这里的工夫实践主体,不限于君主,而是指每一个个体。之所以能如此,其前提就是“万物一体”,天地万物普遍地关联在一起,而人则是天地之灵,承载着“参赞天地化育”的使命,如此人的心的状态决定着天地之心的状态,而人的气的状态也影响天地之气的状态。但要想达到最终的效果,朱子也强调需要达到圣人境地,只有圣人能够最终实现天地之气顺。然而这不意味着普通人不需要做工夫,这也是朱子诠释和汉唐旧说的一大差别。郑氏曰:“致,行之至也。位,犹正也。育,生也,长也。”孔氏曰:“致中和”,言人君所能,至极中和,使阴阳不错,则天地得其正位,生成得理,故万物得其养育。[25]
这里孔颖达认为,能够致中和的主体是国君,而非普通人。此外,对于人君致中和的理论基础,乐爱国教授以为,“我们虽然不能完全肯定孔颖达疏对‘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诠释,依据的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但在孔颖达疏中,的确包含了‘天人感应’思想”[26]。在这些内容上,朱子与之均不同。
首先,朱子讲感应,但不是天人感应的模式,而是强调“心”,“朱子认为天地与人心的关系,不是副本感应,也没有基于天地人参立的前提来‘合德’。他直接先描述了‘致中’则未发之时无偏倚,自然天地位,‘致和’则应物之处无差缪,自然万物育。它意味着人心的‘致中和’与‘天地位万物育’不仅是道理,而且是切实可做的事,即戒惧以守中之事,谨独以能和之事,这就是具体的工夫。……朱子说‘此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显是为了避免被误解有‘天人感应’的意味”[27]。朱子的感应模式完全不同于“人副天数”的模式,没有将君主与天的意志联系在一起。比起天人感应,朱子更强调“裁成辅相”,将“致中和”与“参赞化育”联系起来,饶鲁在解释《中庸》“唯天下至诚”一章时讲:“此与首章一般。至诚尽性,便是致中和;赞化育,便是天地位、万物育。”[28]《朱子语类》言:
“赞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间,虽只是一理,然天人所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种必用人;水能润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熯物,而薪爨必用人。裁成辅相,须是人做,非赞助而何?程先生言:“‘参赞’之义,非谓赞助。”此说非是。
程子说赞化处,谓“天人所为,各自有分”,说得好![29]
问:“‘财成辅相’字如何解?”曰:“裁成,犹裁截成就之也,裁成者,所以辅相也。”(一作:“辅相者,便只是于裁成处,以补其不及而已”)又问:“裁成何处可见?”曰:“眼前皆可见。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圣人便为制下许多礼数伦序,只此便是裁成处。至大至小之事皆是。固是万物本自有此理,若非圣人裁成,亦不能如此齐整,所谓‘赞天地化育而与之参’也。”(一作:“此皆天地之所不能为而圣人能之,所以赞天地之化育,而功与天地参也”)又问:“辅相裁成,学者日用处有否?”曰:“饥食渴饮,冬裘夏葛,耒耜罔罟,皆是。”[30]
天地气化流行化育万物,生生是天地的职责,因天地生生之理而成就现实的生生则是人的职责,天地生生需要人的赞助,正所谓“天人所为,各自有分”。天有天能做的,人有人能做的,这是人的主体性在天的主宰性下的彰显。圣人在其中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圣人能够根据天理,将不恰当的地方做好,能够根据自己对天理的把握,通过“裁成”将天理具体化,进而实现天理的现实性,完成对天的辅相,这就是“参赞化育”。通过这样的主体性活动,完成政治秩序的确立,并最终也让自然秩序得到更好地呈现,这就更加强调人的政治主体性活动对于天地自然的影响,而非天的意志的作用。
其次,朱子强调君主的正心诚意对致中和的作用,认为正心诚意是君主“所能”的基础。这是理学政治哲学的突出特点。上文于此多有分析。
最后,朱子不仅强调君主在致中和、召和气上的作用,还强调每个人在这一效验上的意义,这是理学家普遍的看法。[31]君主要正心诚意,而士大夫则可以“格君心之非”,这就意味着每个人都需要“明明德”。《朱子语类》有:
问:“‘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定,便是天地位否?”曰:“有地不得其平,天不得其成时。”问:“如此,则须专就人主身上说,方有此功用?”曰:“规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随一个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学之为王者事)问:“向见南轩上殿文字,多是要扶持人主心术。”曰:“也要在下人心术是当,方可扶持得。”问:“今日士风如此,何时是太平?”曰:“即这身心,亦未见有太平之时。”(三公燮理阴阳,须是先有个胸中始得)[32]
《朱子语类》该卷解释“致中和”多有类似的表达,此条颇为详细。“致中和”所要达到的状态,在朱子看来并非只有政治上的有序,同时还有自然上的“地平天成”,这与儒家经典中圣贤克服自然的挑战有关。学生以为如此,“致中和”就应当是人君承担的。朱子以为从天下的规模看,应当是人主有所作为,但每个人都应当在自己的使命范围内,尽自己的义务,特别是士大夫应当致中和,并以自己的心性修养扶持人主的心术。在传统儒家经典中,三公有“燮理阴阳”的职责,在朱子看来前提就是三公的心术。针对当时的情景,朱子以为,凭借当时的士风,依据当时士大夫的心术状况,离太平还远,也即离和气被感召到还有一定的距离,可见朱子对士大夫修身与感召和气的关系的强调。
当然,这也就可以理解朱子如何将“致中”与“致和”分开来看:
“致中和。”所谓致和者,谓凡事皆欲中节。若致中工夫,如何便到?其始也不能一一常在十字上立地,须有偏过四旁时。但久久纯熟,自别。孟子所谓“存心、养性”,“收其放心”,“操则存”,此等处乃致中也。至于充广其仁义之心等处,乃致和也。[33]
致中更强调个体的修养,对应《大学》的讲法是自明明德,致和则强调扩充、扩展,对应《大学》则有“明民、明德”,即新民的意涵,也就是致和更强调政治性的实践活动。在《大学》的逻辑里,明德为本,新民为末,如此在《中庸》的逻辑里,致中为本,致和为末。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在朱子看来,能否感召到和气,实现自然的和谐,不仅仅是道理如此,而是“理必有事”,“中和位育”是实事,这与朱子的历史观密切相关。《中庸或问》讲:
曰:“天地位,万物育,诸家皆以其理言,子独以其事论。然则自古衰乱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万物之育,岂以是而失其常耶?”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则不必天翻地覆,然后为不位矣;兵乱凶荒,胎卵殈,则不必人消物尽,然后为不育矣。凡若此者,岂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诬哉!今以事言者,固以为有是理而后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为无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备,有以启后学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为尽耳。”(6,559—560)
朱子认为灾异、战乱都属于天地不位育的变现,这显然是站在比前代儒者更高的标准上看待“中和位育”,在此标准下,三代之后的所谓汉唐之治便都不能被称为“致中和”。清代朱子学者吕留良将朱子这一诠释背后的历史意识充分揭示了出来:
位育是实事,此理先信不及,不得不倒说入虚空去。只看末世俶扰汩陈,灾沴夭疠,上下咸失其所,不可谓非圣人之咎也,若得个圣人出来,从头经纬一番,其气象又何如?若谓今日天地万物未尝不位育,即是汉唐以后之天下未尝不三代,不知圣人之所谓位育,不是此境界,所谓三代之天下,亦不是此境界,读书人胸中须先有此境界始得。[34]
吕留良以为配资杠杆什么意思,圣人去治理天下,气象一定不同于一般的末世。汉唐情景也非“中和位育”。达到三代情景,一定不仅仅是小康的局面,三代那个理想的世界,即含有政治上的有序,也一定包含着自然境况的和谐美好。这可以说是朱子在谈论“感召和气”“致中和”时的应有之义。